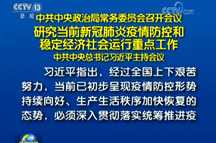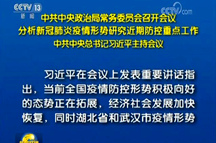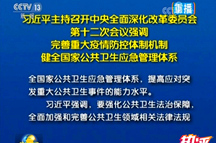老邪:马钢宪法,还是鞍钢宪法?——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历史经验

【转者按】这是一位朋友的文章,转发以供探讨。
一、关键节点回顾
2020年2月7日,《经济观察报》发了一篇文章《武汉时间:从专家组抵达到封城的谜之20天》,较为详细的回顾了2019年12月31日到1月20日关于新冠肺炎的发现、上报、确认、公布,最后到武汉采取“封城”措施的过程。如果这篇东西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12月29日张继先医生即上报疫情。武汉卫健委就内部发文,要求辖区内医疗机构立即清查统计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国家卫建委的工作组和专家组12月30日即到达武汉。2020年1月1日,武汉市采取措施关闭华南海鲜市场。国家卫健委成立了由主任马晓伟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会商分析疫情发展变化,研究部署防控策略措施,及时指导、支持湖北省和武汉市开展病例救治、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
心平气和地讲,这一系列操作,不能说不及时。
中间有一个插曲是武汉公安部门传唤了8个人。但是,我认为传唤与不传唤,对于疫情防控的发展而言,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即便不传唤,这8个人在私底下传的信息,也有一个发酵时间,也不会立即引起广泛的重视,更不可能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合理部署、采取统一的防控行动,更大的可能是制造恐慌和混乱。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在这个时候,国家卫健委和地方政府已经介入了,因此,他们接下来的决策部署才是有决定性的。
我认为,这篇文章传递的最为重要的信息是这样几段话:
经济观察报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危重症专家、副主任医师余昌平的采访中得知,早期新冠肺炎“确诊是很难的——需要专家、领导签字,才能查冠状病毒”。
而财新网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的采访证实,此前,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到武汉金银潭医院调查后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但一线医生反映,这个诊断标准太苛刻了——
“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检测;这样很容易漏掉真实的病人。而这是传染病,确诊标准弄得太紧,放掉有病的人,对社会危害很大”。
直到后来国家卫健委派的第二个专家组1月18日到武汉后,诊断标准发生变化,确诊病人的数量就急剧增加了。
……
15日,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一级响应。这是公共卫生响应的最高级别,意味着事情“特别重大”。
对于是否人传人,1月16号武汉通报中改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低”。
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组长、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徐建国院士,1月16日在接受《Science》采访时也表示:这是一个有限的感染,763名密切接触者无一发病。
1月17日,武汉卫健委没有通报。
根据《财经》杂志1月27日的报道,也正是在这一天,港大深圳医院的临床微生物及感染控制科主管袁国勇,将临床病例中发现这种新型肺炎人传人的消息,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和广东省疾控中心做了通报。并且,作为新冠肺炎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他也将此信息透露给其他专家组成员。
当日,湖北省“两会”闭幕。
从18日开始,武汉卫健委采取隔两日通报的方式:18日通报称,16日利用国家刚下发的诊断试剂盒检测、认定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例。19日通报,17日新增17例。20日公布了两天的数据——18日和19日分别新增59例和77例。21日通报20日新增病例60例,回到隔天通报。此时,武汉通报的累计病例258例,死亡6例。
这也是武汉市卫健委最后一次通报疫情信息。
武汉市官员后来表示,1月16日前,湖北省没有检测试剂盒,病例确认的流程是:临床检查、会诊确认疑似病例后,还需采样由区、市、省层层转运到北京国家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病毒分离和核酸检测,结果返回约需要3~5天。在此之后,病例样本送到湖北省疾控中心检测,检测时间缩短到2天左右,每天可检测样本200多份——这在日后疫情大爆发时,又严重制约了确诊数量和进程。 今天(2月8日),网上的舆论已经有把矛头针对国家卫健委专家的了。这并不奇怪。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追究哪个个人的责任或者找人出来“背锅”的层面,那这种反思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而且,对于下一次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并没有什么帮助。
怎么样才算能有帮助,或者有所启示和反思呢?
从引用的这几段来看,问题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卫健委的专家制定的三条确诊标准是否合理?一个是来来回回的病毒确认过程是否合理?
但是,我们只要稍微再思考一番,就可以明白,这两个焦点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国家卫健委是否认为这个事情很严重?这是一个判断题。但是,国家卫健委没有快速地给出一个决断,但同时,“15日,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一级响应。”而“1月16号武汉通报中改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里缺少的是一个决断,无论是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还是地方政府的官员。但是,对这两个主体而言,他们其实都有各自的“苦衷”,或者说有各自的说法:专家可以从专业的角度说,确认一种新型病毒本来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中间有一系列的科学流程和操作流程;地方官员可以说,这种科学问题他们并不懂,他们只能听专家的,专家说严重了,他们就按照严重的情况来应对。其实,从这篇文章的时间线索也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很早就已经介入了,并且和国家卫健委基本上是同步进行反应的。
如果事情分析到这个地方,按照一般的思维,似乎就该把两个地方的一些人弄出来承担责任。我认为这是把事情想的过于简单,而我真正试图去思考的问题才刚刚开始:
从整个操作流程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一切都是按照正常流程来的。29日医院上报情况,地方政府立即动手排查,30日国家卫健委的专家就到了。再到后面,也都是按照流程来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有人说,出在“三条标准”。但是,我认为,对于专家们来讲,标准越严格,才能把事情搞的更清楚。这是一种正常的科学思维、技术思维。
真正的问题在于: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防控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但是,我们在应对很多问题的时候,往往采取单纯的技术思维。比如,国家疾控在非典疫情之后,建立了一套网络直报系统,但是,据《经济观察报》2020年2月3日的文章《SARS之后国家重金打造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为何并未及时启动》显示,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间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当初搞这个系统的初衷,恐怕是担心层层上报中间出现瞒报和不及时上报的情况,因此,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第一时间直报,人们认为只要有了直报,国家卫生部门第一时间知道了,我们在传染病防控上就可以赢得宝贵的时间。但是,这样考虑问题还是单纯技术思维,还是太过简单。不管技术上把上报速度提高的多快,在应对这种带有半未知性质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最难的地方的是决断。
二、应当重视的历史经验
在这次疫情出现以后,舆论上立即开始发酵关于疫情防控延误的话题,而这类话题又很容易发展到指责一些人、一些部门瞒报、拖延、官僚主义等等话题。但是,我第一时间的判断,却不是这样。我认为这里面有机制问题,尤其是看到《经济观察报》梳理的这个时间线索以后,我更加坚定我的看法。
需要强调的是:我说的是机制,不是体制。
体制是静止的,体制只能在日常状态中起作用。而突发事件,尤其是较大的突发事件,其本身就不是日常状态,而是一种非常状态。面对非常状态,任何日常体制都会遭到冲击。如果这个时间线索的梳理没有重大遗漏的话,我们可以说:就疫情防控体制的设计而言,这里面没有什么重大失误,人们都是在这套体制中按部就班各司其职的活动,没有人有什么重大失误。但是,就对疫情防控本身来说,却延误了战机,失去了宝贵的时间,使得疫情扩大化。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里面不是哪个个人犯错的问题,但是,实际的情况超出这套体制的掌控范围,也就是说,体制本身是死的东西,是上层建筑的东西,实际情况复杂的多,没有任何一个包治百病的体制,也没有一个一经建立就一劳永逸的体制,原因很简单,现实是无限可能的。疾控中心的网络直报系统不可谓不先进,但是,新型冠状病毒却在那套系统里面没办法被表达,人们对该病毒的命名也是今天(2月8日)的事情。
那么,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什么样的机制能够更好的为应对突发事件服务呢?从逻辑上讲,既然任何体制都是很容易被规范化、流程化的,也可以说是精确化、科学化的,但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僵化的(因为,我们设计任何制度的前提都是基于当时的认知状况,而现实往往超出我们的认知状况),那么,我们所要求索的某种机制必定应当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或者说弹性。
因为,我本人经历了5.12汶川地震,当过地震的灾民,因此,一度对地震预报的话题非常有兴趣,找了不少材料和论文来看。我惊奇地发现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地震工作搞得有很成绩,并且,很有特色。我认为,这些历史上的宝贵经验,可以提供给我们当下来参考,给我们探索一种更加有效的机制带来一定程度的启发。
如果把地震灾害和传染病疫情灾害都看做是突发事件的话,地震的突发性更强,从预防的角度来说更加困难,很简单,因为地震的预报问题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解决,所谓没有解决,指的是没有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方法或者发明一个普遍适用的仪器,准确预报地震发生的准确地点和时间。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中国的地震预报一直是坚持一种“边研究、边预报”的状态——这是一种强调实用性的思维,但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干脆就不搞地震预报了,而这体现的就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思维:既然没搞清楚预报地震的全部机理,那干脆不搞了。从技术上讲,地震预报这种现状,相对于传染病疫情防控而言,要差的多。毕竟传染病疫情爆发有一个可以摸索和直观的过程。对于防疫而言,大多数情况下是量的问题——10个人被传染,还是10000个人被传染;而对于地震的预报而言,却是一个质的问题——几分钟几十秒的时间内,要么救了千百万人的命,要么千百万人丧命——因而,这种突发性和严重性表现的比之疫情更加极端。因此,地震预报机制有一定参考意义。
1966年邢台大地震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十年的地震活动高潮期,中国的地震预报工作也是有了血的教训才真正起步。邢台地震后不久,震区人民就自发组织起来,组成观测小组,像站岗放哨那样日夜监视着各种异常现象。周总理肯定了这一创举,指出不仅要有专业队伍,还要有群众队伍环绕在专业队伍周围。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结合相关职能部门、科研单位、科研人员几年的努力,最终在1972年全国第二次地震工作会上总结归纳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地震工作总方针(1975年海城地震后,做了一些修改,强调要“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防工作。”),专即指专家,群即指群众。
在这样的工作总方针指导下,成绩如何呢?“过去三四十年里,各级分析预报部门、广大台站以及业余测报人员,与直属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起,坚持‘边研究、边预报’,取得了……20次预报成功的震例。虽然预报成功的次数还不多,仅约占同期地震次数的10%,但这些预报意见都上报有关政府,采取了一定程度的防御和应急措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减灾实效。这些成绩不仅令从事地震监测预报和研究的技术人员振奋,深受鼓舞,而且给政府官员和老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多次受到各级政府的表扬和嘉奖。”(韩渭宾《“边研究、边预报”利弊分析与发展建议》,《国际地震动态》2005年5月)这些预报成功的案例中,比较大的,也很著名的就是1975年海城7.3级地震,1976年龙陵7.4级地震;1976年松潘-平武7.2级地震的预报。
专家和专业队伍按下不表,群测群防、专群结合的“群”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以四川为例:四川省的地方地震工作始于1970年,当年建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地震办公室。之后,四川省革委会发出(70)148号文,要求有震情的地、市、州、县建立地震工作机构。同年8月、9月,马边县地震办公室、茂汶(今茂县)县地震办公室测报组率先建立并开展工作。1970年3月至1971年底,雷波沙坨、壤塘、马边连续发生了8次5.2—5.9级地震,西昌、甘孜、阿坝、凉山、渡口(今攀枝花)等地、市、州和20多个县相继成立地震工作管理机构,并在一批学校、气象站、林牧场、邮电所、广播站、农场、矿山和知青点建立了地震测报组织,马边中学、西昌礼州中学、西昌一中、冕宁巨龙中学、泸定中学等还结合教学成立了地震科研小组,开展地震业余测报。1974年6月,四川省革委会以川革发(74)66号文件转批《四川省1974年度群测群防地震工作计划要点》,进一步推动群测群防工作。1974年底,全省已有11个地市州和50多个县建立起了地震工作管理机构,31个县有单位代管地震工作;群众测报点发展到500多个,各类简易观测仪器700多套(台),测报人员1600多人。自贡、茂汶、平武(流动台)、新康石棉矿、岷江齿轮厂等地方台、企业台和众多的群测点围绕在专业台站周围,地方群众测报队伍逐渐形成。唐山地震后,四川各地又建起大批测报点和宏观点,群测群防队伍达到高潮。至1976年年底,全省有微观测报点1130多个,观测员5770多人;宏观点2410多个,观察员7930多人。这批群测点分布在四川境内东经106°以西的广阔地域,为预测预报松潘-平武7.2级地震和盐源-宁蒗6.7级地震提供了丰富的前兆信息。(见郭安宁《中国十年天灾备荒史1966-1976》,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482,483页)
数字也许太过抽象,仅举松潘-平武地震的预报为例:
1976年上半年,四川出现了严重震情,省地震部门提出在松潘、茂汶一带可能发生6级或6级以上地震的趋势预报意见。6月中旬,大邑、邛崃、天全、宝兴等县出现了一批以地下水变化为主的宏观异常。7月20日前后,沿什邡、绵竹、彭县、灌县、茂汶、安县一带群测点报告,发现大量火球、地光、地下水和动物等宏观异常现象。地震专业人员去到现场进行一一核实,为地震短临预报提供了资料依据。8月5日至6日,省地震部门连续召开了绵阳、温江、成都有关地震台、分析预报人员和地震办公室紧急会商会,根据专群近期观测的各种资料和各类宏观异常资料,分析研究后,指出在8月份,特别是8月13日、17日、22日前后,在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茂汶、北川或康定、泸定一带可能发生6级或6级以上甚至7级左右地震。平武地震台根据小震活动在8月初期突然平静,以及本台水氡异常,坚持认为发震地点在松潘、平武一带。8月7日至10日,青川、北川、安县、灌县、绵竹、彭县、江油、名山、宝兴等30多个县的群测点观测的简易仪器、精密天平仪出现突跳,指针摆动;宏观点发现地下水、动物(牛、马、猪、狗、鹿等)异常以及地光、火球和地气等(仅地下水异常就有390多起)。省地震部门根据专业台站异常资料和宏观异常分析,认为临震现象明显,震情十分严重,两次紧急报告中共四川省委和国家地震局。8月12日凌晨,省防震抗震指挥部,四川省地震办公室紧急电话通知各级地震办公室、各专业台站、群测点,各有关地区立即进入临震戒备状态。绵阳、阿坝等地、州各县采取了紧急防震措施,动员民众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8月16日22时06分,松潘、平武间发生7.2级地震。由于有了前次地震预报经验,专群地震队伍又及时预报了22日6.7级地震和23日7.2级。震前有预报和预防,减少了人员伤亡。(见江在雄《1970—1976年四川地震群测群防实践》,《四川地震》2007年3月)
实际上的预报过程中间,故事更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找相关资料来看。但是,这里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
三、几点启发
这里防震工作的历史经验,并不是要让防疫部门也复制一下就拿去用,而是要让大家受到启发。
写这篇东西比较仓促,初步的启发有以下几条:
第一,前面谈到了“决断”。地震预报当中,最难的恐怕还不是预测本身,而是预测了一个结果出来以后,由决策者做出决断。在我接触到的很多论文和材料当中,这些搞地震预报研究的人,往往谈到领导人的担当问题,领导人如果没有担当,专家给出预测,恐怕也下不了决心采取行动。在专家方面,也有决断问题,那就是专家从专业角度做出决断,给予决策者以决策依据,这难道不需要担当吗?当然也需要。而实际上,我们看到武汉的疫情中间,担当的一面是有所欠缺的。地方官员依靠专家意见,专家却只是在形势的逼迫下作出判断。
第二,上面一条谈到的担当问题当然至关重要,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管是专家的研判,还是决策者的决策都不可能是凭空的。从我所举例的“专群结合”的地震预报成功案例中,就可以看到,专家的研判和决策者的决策都是建立在有大量信息汇集的基础上的。这些信息有专业的,有非专业的,有宏观的、有微观的……也就是说,在一较短的时间内,汇集和占有大量信息的情况下,经过分析做出的决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注意:我说的是正确,而不是科学),这也是专家和决策者敢于决断的根据。因而,这使得我在看这些历史材料的时候,不免惊赞于各个层级的干部(省市县社队),都是那么的敢于做出决策,敢于让群众采取预防措施。这些决策不见得都正确,也有发布了地震预报,结果没有地震而造成经济损失的例子,但是,与人民的生命安全相比,经济损失是其次的问题,群众会在事后骂骂娘,会编个“辽人忧地”的笑话,但这些相对于人命来说,都不重要了。
在武汉疫情爆发时,国家卫健委的专家并不大量掌握各类信息,他们仅仅掌握从技术角度切入的医院上报的病例信息,并将这些病例取样拿去实验室检验。从科学的角度和技术的角度说,这一系列操作,无可挑剔。甚至他们的语言表述也是精准的,一个时期内,关于有没有人传人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但是,在排除瞒报的可能性以外,“没有证据表明有”,一种可能性是真的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明明有,但你们不掌握。无奈的是,现实情况是后者。为什么呢?就在于专家所得到信息的渠道太单一了,虽然,疾控中心的直报系统下到乡卫生院,但是,范围都在卫生系统内部,而没有延伸至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比如药店、小诊所、学校医务室……这些地方可不可以想办法监控,或者从这些地方掌握一些信息呢?这些信息未见得一定是要确诊新冠肺炎,这些信息完全可以是感冒药的销售量,小诊所的接诊量等等,都是可以帮助决策的。
但目前这套体系始终是以技术思维为核心的,他们始终强调要确诊、要确认是不是人传人后,才做出决断。地方官员也是一样的,如果地方官员有更加丰富的信息汇集,而不仅仅只有来自专家的最终的科学认定和医院按照流程的上报数据,即便是没有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也完全有理由作出决断。
第三,就是前面提到的,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防控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防控方法局限在科学技术范围内。群测群防的地震预报实践提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经验的重要性。经验的东西,不见得都立即会被科学所证明,但是,经验同样可以作为决策依据来使用。张继先医生最初的判断难道是建立在清晰的科学实验结论上的吗?不是。她是根据她的经验做出的判断,并且在她所在的科室采取了措施。但是,这个判断进入了以技术思维为主导的疾控体系之后,大家都在等疾控专家反馈意见,而这个经验判断没有被纳入到决策依据当中。这里我们不要教条地理解“专群结合”的“群众”,好像只有普通老百姓才叫群众。其实,相对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来说,一线医生就算是群众,为什么会有8个医生提前往外面发出提示信息呢?不就是因为他们在一线,更了解情况吗?还有,“三条标准”明显在一线缺乏可操作性,但是,作为一线医生的群众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发言,或者说,在这套体系当中,对于疫情的研判和决策,他们根本就缺乏发言权,他们只能按照流程上报信息,等待上边的意见,如果专家组研判失误,也只有等专家组自己来纠正自己,他们自己缺乏主动性。专群结合的核心之点,恰恰在于广泛的调动积极性,有了积极性,才会有主动性。
总结起来说,实际上,只有更加深入贴近群众的现实生活,并且,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各方的能动性,才恰恰是应对突发状况中,具有弹性的反应机制。但是,很遗憾的是,包括后来的地震工作,指导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比较过分的强调了科学性,用官方的话语讲,叫做“把地震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地震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建设上来”(《当代中国的地震事业》,92页),落实起来,实际上就是逐步淘汰了不够科学的“群防群测、专群结合”的实践。从逻辑上讲,这条路径推到极致,就会变成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只搞地震预报研究,而不搞地震预报实践。但汶川地震后,一部分搞地震工作的人认为“地震预报很难,但不能不搞”,又开始对“群测群防,专群结合”的实践进行回顾,并且,提出“要研究市场市场经济环境下,怎样发展与巩固群测点,如何切实做好专群结合”的问题。(韩渭宾《汶川地震后的几点思考》,《四川地震》2010年12月)
最后,事起仓促,只不过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错漏、外行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题 注:
“马钢宪法”,是当时苏联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的管理办法,即实行集权化管理,搞物质刺激,依靠少数专家和繁琐的规章制度,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这一管理规范在苏联得到了高度认可。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这一管理模式与中国国情渐行渐远。
“鞍钢宪法”,是我国鞍山钢铁公司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相对立。
——编者加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
- 文章
- 精品课程
- 课程方案
- 教育机构
- 名师荟萃
- 有问有答
问题反馈
问题描述
请输入问题描述内容
当前已输入0个字符, 您还可以输入1000个字符